今年是只有我和母亲的团圆,可我希望独自一人,不愿成为她的累赘,她本应回到她的故乡。
2021 年 2 月 12 日首发于 Yeol’s blog
去年的今天,我在宾馆的窗里看烟花。
那是个烟花绚烂的城市,不像这里,但我不属于那儿,烟花也仿佛为了远离我而飞上天空。
我看着玻璃上的人影,它的头部爆炸了,绽放出绚丽的花。
烟花只在天边升起,嘭,然后落下或是消失。
电视内放着春节联欢晚会,声音调得最小,隔着屏幕一些彩色的方块在跳跃,在倒计时,跟随着父亲的呼噜声前进。
我攥着口袋中的口罩,想把它丢出去,但玻璃就在前面。玻璃上的人影又爆炸了。
一切都不属于我,都在隔离,在逃跑。
窗外是烟花盛世,但这不是我的城市,就连烟花都隔着无数建筑,和一块玻璃。
我的城市在哪?我知道,远方。我不想念那里,那里没有我值得留念的人和事,我很嫌弃它,可就是这么差劲的它也在离我越来越远。这里快要封城,我们回不去的。
过年的喜悦气氛属于银幕内,他们的倒计时我只觉得越来越难过。一秒,一秒,一秒,第二年了,我又顺利度过了一年吗?是的。不,不是,我只是又度过了一年。接下来呢,便是再一年。
本来不会去旅游的,但这是少见的能凑齐全家三人的机会,他们想一起去,不论因为什么,都很稀有,我便也有必要答应了。下这个决定非常艰难,我在一月初听闻新冠消息,大家不太在意,非常不在意,而我过敏了,买了好几大包口罩,酒精,纱布。纱布干嘛用?我不知道,但我不买会很难受,我要把没用的东西也给备着。现在说要去旅游,无法拒绝的旅游,要做飞机,要做车,要与人接触。答应时我装作高兴的场景,至今想起都感到灵体分离。整个过程也十分煎熬,我没法享受任何一个景点,我只希望下车,去空气新鲜的地方,摘掉两层口罩,计算着回宾馆的时间。大巴车上,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,画画吗,我拿了笔和纸,但我没拿会画画的手,我没有。我想睡觉,不困,但我需要,可导游说:不要再睡了,相信大家也不愿「上车睡觉,下车拉尿」,既然您选择我们这个高端的….
我把母亲拍醒,她不理会,合眼,睡着了。
年夜饭是 N+1,我是那个 +1。他们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,想要在异乡找到团圆的感觉。但我讨厌他们,因为病毒,因为我不认识他们。所以我很快地吃了几口,走了。走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,摘下口罩吸几口气,远远地望着灯火被人影冲散,消失,又聚拢。
年夜饭当晚,回到宾馆,我想到自己连年夜饭都没吃饱,不禁觉得有点寒酸,可这都是自己作出来的,要惩罚谁?
我的脑袋爆炸了,这次是红色的花。
母亲凑近,望着窗外极轻地说:新年快乐。
「嗯,新年快乐。」
我拉上窗帘。
今年是只有我和母亲的团圆,可我希望独自一人,不愿成为她的累赘,她本应回到她的故乡。
年夜饭极其丰盛,我和她做了 12 道菜,她说这象征着 12 个月,但我知道这些其实只代表着十二个仪式感,为了找寻年味。结果 11 道菜都在做齐前凉了,只有一道汤还保留着一点点温度。
我说:「这样,今年就是冰冷的一年了。」
她说:「别瞎说。」
我喝了一口酒:「是,没错,还有一个月在路上。」
她说:「那你赶紧吃那个热的。」
我说:「不了,我希望那个月是最后一个月。」
我们的饭量都很小,基本上没有动几口,但吃了很久。因为她要编辑视频,她要把这么温馨的一桌子菜分享给其他人。而我感觉,我在把她分享给其他人,或者割让。
我的脸红了,很红很烫,我一喝酒就会这样。她要给我拍照,我说对不起,算了吧,去拍新一年的我吧。
她要看春晚,但我看不下去,于是我们还是回到了各自的房间,关上各自的门。直到新年钟声,我们才又见面,问句新年快乐,互换红包,她想睡觉,结束了。
我不知道这几个小时她在房间里做些什么,我也没有空去想。我在这几个小时内,经历了几次失败,对于我设定的目标的失败,比如躲避一些难缠的人际关系,躲避一些难缠的人际关系,和躲避一些难缠的人际关系。我想,今年的最后一天,我要把联系方式断开,我要清净,我要远离所有人。很显然没给今年开个好头,那些关系变得更加糟糕了。
我把社交软件下载回来,发现收到了很多的「新年快乐」。
新年快乐,大家都在祝福这个,我也只能祝福这个。可是我不希望再收到这样的祝福了,毕竟我的身边没有女巫,没有谁能给我预言或者诅咒。「新年快乐」就像是个目标,你要以「新年快乐」为目标活下去,带着我们的祝福一定要快乐。
一定要快乐吗,别这样吧,我希望能够快乐地生,快乐地活,快乐地死,但以此为目标就太难了,实在做不到那就做不到吧,难以触及的目标只是折磨。
新年,你要快乐,吗?不,我可以快乐,但我不追求它,无论怎样,只管接受,就这样不带任何期待,迎接每个明天。
19’8
Yeol 不喜欢做自我介绍。她在互联网上的某处给自己置办了一个垃圾桶,我们姑且也归类为博客。其中或能拾得可成片段的闪光絮言,当然对世界上的那么多人来说可能并无大用。
19’8 指的是 2019 年 8 月,Yeol’s blog 的建站日期。具体日期已失。
这篇文章暂未有版权声明。未来使用请参阅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的合理使用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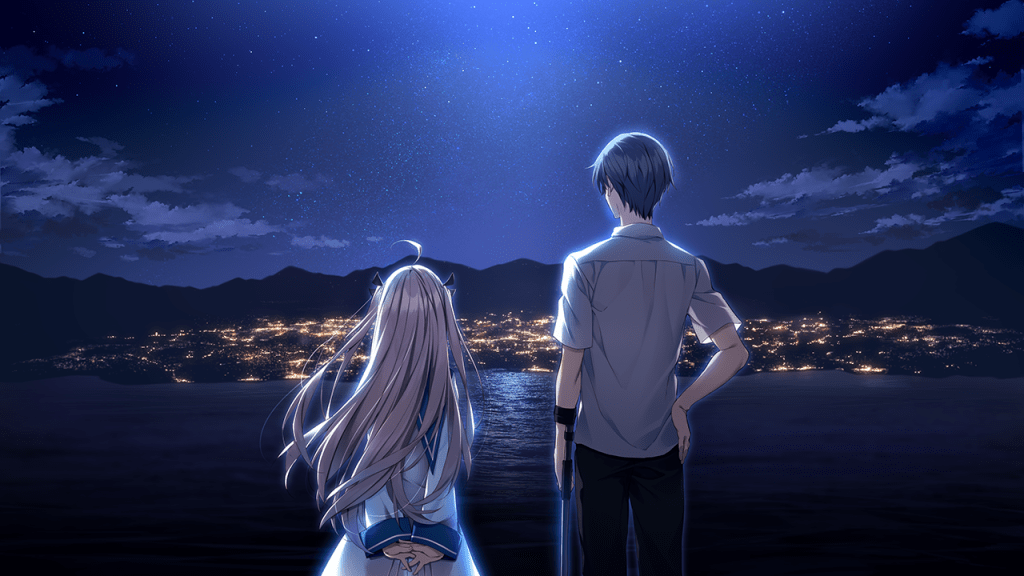
留下评论